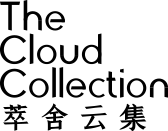延伸阅读: 乔纳森·普西耶对话大卫·克拉耶博《五彩纸屑》
 “时间流—大卫·克拉耶博和周滔”展览现场,萃舍云集,2025-26:大卫·克拉耶博,《五彩纸屑》(2015-2018),双频影像投影、3D动画(彩色、无声),18分25秒 ©萃舍云集
“时间流—大卫·克拉耶博和周滔”展览现场,萃舍云集,2025-26:大卫·克拉耶博,《五彩纸屑》(2015-2018),双频影像投影、3D动画(彩色、无声),18分25秒 ©萃舍云集
乔纳森·普西耶对话大卫·克拉耶博:五彩纸屑
原文发表于汉尼拔图书2022年出版的书籍《镜头之寂》(The Silence of the Lens)。 本文中,JP代表乔纳森·普西耶 (Jonathan Pouthier),DC代表大卫·克拉耶博(David Claerbout),以下内容均以此简称指代。
(JP)五彩纸屑自上空倾泻而下,某个未具名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们正在庆祝着或许是一场选举的胜利。然而,这种集体性的、近乎狂喜的欢腾却异常寂静,仿佛被凝固在时间之中。通过进入政治再现的场域,《五彩纸屑》激活了一种高度程式化且刻意戏剧化的图像。矛盾的是,我们知道这类再现往往不会直接呈现任何实质内容。问题始终在于如何超越这种模式化构图的视觉秩序,并探测其中蕴含的意义层次。这种从政治戏剧化中借鉴而来的图像叙事体系,究竟向我们揭示了什么?

大卫·克拉耶博 《五彩纸屑》(2015-2018)影像截图 双频影像投影、3D动画(彩色、无声) 18分25秒 图片来源:艺术家和施博尔画廊柏林/巴黎/首尔, ©艺术家
(DC)《五彩纸屑》的场景设定在一个未被指明的政治活动中,可被比拟为“选举之夜”。纸屑被抛向空中,似乎正在庆祝某种胜利。若从政治思维的角度审视,这种没有具体日期与署名的模糊情境会引发某种不安,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定位自己与这些庆祝性图像之间的关系。就形式而言,整个场景以一条水平轴标示着上与下、光与影之间的分界。纸屑将前景完全填满,并作为一个“协商者”在画面上下两部分之间起作用。尽管画面被分割为两个截然不同、带有象征意味的层级,而且被强烈对比的对立所标记,这一构图仍然显露出某种关于共同体的观念。
毕竟,彩屑纷飞的场景总是象征着欢庆与凝聚的时刻。这一想法早在我先前的作品中就已存在,例如《阿尔及尔欢愉时刻的切片》(2008年)。当时我试图通过一组栖居在阿尔及尔城堡区屋顶的年轻人群像,以及对于现代性理想中关于未来、自由与光明等概念的审视,来解构这种理想化图像。重要的是让两种对立视角在同一镜头中共存,揭示构成图像的多重意义层次。
 《五彩纸屑》(创作流程截图)
《五彩纸屑》(创作流程截图)
(JP)这类政治再现在定义上具有规范性与修辞性。您本人也将这种图像叙事体系描述为简单化且直白化的。然而您的影片却正是关于这些完全被建构的图像。这种象征主义且理想化的视觉秩序中,吸引您的究竟是什么?
(DC)《五彩纸屑》完全契合“如画”(Picturesque)美学的表现范式。这一点在尤其体现在对光的处理上,充盈着画幅的彩屑使光线产生破碎效应。于我而言,最根本的创作动机源于与光线互动的单纯渴望,以此改变再现的视觉秩序。从某种意义而言,彩屑在我看来是像素的完美具象化呈现。它明晰化了图像与数字投影的像素化本质。这是一种“镜像嵌套”(mise en abyme),将人工光线原子化为无数的粒子。最终,片中的群演不过是在凝视他们自身图像的像素化。
乍看之下,《五彩纸屑》的图像刻意保持简约,甚至可以说是直白的。似乎只需要一眼便可把握其内容。尽管这一场景在时间、地域与意识形态层面均保持不确定性,它与此类图像的“通例”相似,已是我们集体想象中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之所以认为它们“过于简化”的原因。它们既基于我们对其的记忆,也基于我们对屏幕画面的当下感知。换句话说,对某一场景“亲历经验”并不必然优于我们对于它的“观念”。 这实质上意味着观察行为是基于对事物的先在概念,而非基于具体经验反过来形成认知。大概也正因此,这些图像在我们看来才如此图式化。我们不妨追问:一幅图像何时“如画”?是否正是在图像完全并入这种图式化的视觉秩序、并且不再与视觉感知中那些出其不意之物有任何关联的那一刻?

大卫·克拉耶博 《五彩纸屑》(2015-2018)影像截图 双频影像投影、3D动画(彩色、无声) 18分25秒 图片来源:艺术家和施博尔画廊柏林/巴黎/首尔, ©艺术家
(JP)彩屑属于狂欢节传统,是娱乐意象上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在您的影片中,它既阻隔了视线向前景之外延伸,又消解了场景本身的张力,仿佛我们面对的是一幅经过伪装的图像。为何选择将其作为影片的核心主题?政治意象与娱乐意象的交汇产生了什么?
(DC)这部影片的创作首先源于打破常规视觉秩序的绘画性愉悦。彩屑这一象征,使我得以重新启动表面与深度之间张力这一常见的绘画原则。通过填满前景的构图,纸屑使表面变得扁平化。我也认为纸屑既抗拒镜头的自我中心视角,也抵制任何将其行为理性化的企图。它的运动不可预期,无法用固定坐标在时空中被准确刻画;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视觉失序的媒介载体。我也尝试通过彩屑诱发一种“垂直趋向”,既能将场景向上拉升,又突显了构图在重力与失重之间的割裂感。通过精准介入光的现象学,我尝试去去逆转“轻盈”的原则。当光与彩屑交融,最终生成一个明亮的图像并诱发两种对立的色调。因此,这种光源既呈现出笼罩孩童时的暴力性,又在照亮其他人物时显出庆典般的欢愉,如同目睹烟花工厂在烈焰中升腾的奇观。当然,彩屑也承载着一种政治化微粒的隐喻:蓝、白、红三色在集体想象中极易令人联想到法国或美国国旗。
通过这部影片,我想将图像的多重层次显化,并把注意力引向支撑再现秩序的意识形态性权力关系。这种创作手法刻意呼应“觉醒”(woke)思潮,即要求感知并剥离通常相互叠压的图像层级。在《五彩纸屑》中,光如同重负般沉入黑暗,悖论在于:通常象征轻盈的光在此却施加着重力。我的创作意图正是运用这种刻意夸张的意象体系,而彩屑仅仅强化了这种夸张现象。
 《五彩纸屑》(创作流程截图)
《五彩纸屑》(创作流程截图)
(JP)这种图像学上的夸张使得您得以直接点明潜在文本与视觉秩序的本质。您所采用的这种过度审美化的机制实则是邀请我们穿透图像的表面进行观看。这是否意味着通过视觉诱惑引导观众自行解构再现?
(DC)《五彩纸屑》完全在摄影棚内完成。画面中的人从未真正共存过。屏幕上彩屑是一种把“图像的母型”转向“云的母型”的方式。我始终相信图像与云团具有相互溶解的特性,正因如此,漂浮在空间与镜头纵深的粒子概念深深吸引着我。它们能在构图中瞬间引发轻盈的“指数”。
 《五彩纸屑》(拍摄现场)
《五彩纸屑》(拍摄现场)
整个场景建筑的几何结构—以德国本泰姆城堡的建筑形制为蓝本(曾于十七世纪被雅各布·范·鲁伊斯达尔绘入画作)秘密扫描后数字化重构—采用3D技术生成,以便精准控制光线。我的意图是召唤寂静、光与轻盈感,这些在绘画传统中始终是如画风格的经典元素。此外,建筑的哥特式调性也绝非偶然。我刻意让这个空间呈现出教堂般的视觉特质。
然后孩童无声的呐喊与父母愕然的神情将视线引向下方。正是在这无音之喊的瞬间,我们意识到彩屑构成了一道“铁幕”。彩屑不再协调图像各元素之间的关系,而是将人物与场景割裂,阻隔观者的视点。立体派追求多视角呈现以获取最完整感知的雄心依然存在,但在影片推进中,那些在空间维度上愈发清晰可辨的元素,最终都走向了分裂。
 《五彩纸屑》(创作流程截图)
《五彩纸屑》(创作流程截图)
(JP)当构图似乎围绕纵横坐标(即空间处理与时间线性)而建时,彩屑仿佛逃离了镜头的组织。它在视觉秩序中引入一种随机维度,并干扰图像的解读。您希望通过这种既吸引又挫败凝视的处境营造什么?
(DC)影片的叙事框架通过这些将视线向上导引的图像变得具象化。我借鉴了这种古老的构图原理,它基于绘画领域某种特定的戏剧化处理。前景中无处不在的彩屑阻碍了对场景的清晰阅读,使视线无法在镜头中确立方向。我认为这种挫败感也可能源于影片中缺乏情节推进。时间仿佛被悬置,彩屑和群演缓慢到近乎不可察的运动,实则强调了剧情与故事发展的不可能性。更为直白的寂静发生在一个小男孩开始呼喊而无人能闻之时。事实上我们希望能够听到这被排除在连续静默图像之外的呼喊。这种求而不得的体验同样构成了强烈的挫败感。在《五彩纸屑》中,我们试图理解一个持续被碎片化的空间。
 《五彩纸屑》(创作流程截图)
《五彩纸屑》(创作流程截图)
(JP)如果说前景被悬浮的彩屑云团所阻隔,那么背景则清晰地围绕着尤其强烈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层面的对抗性矛盾而组织。通过强化构图中的这种割裂感,您实际上激活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看模式:我们既可以停留在图像表面沉浸于视觉狂欢,也可以选择忽视其天真浅薄的表象以探求深层隐喻。
(DC)彩屑如同雪景般笼罩整个场景,使所有人物凝结在一种共存的静止之中。孩童的无声嘶喊在构图中制造了不谐和,标志着两种决然不相容的观看模式的存在。其一是沉醉于场景内部自我欢庆的绘画性凝视;其二则是可称为“觉醒”的改良性凝视,它使潜在叙事显性化。我想到肯·威尔伯(Ken Wilber)提出的“螺旋动力学”模型。人类发展犹如倒置的圆锥体,螺旋阶梯从本能、传统、暴力、权威与实用主义,逐步攀升至后现代思维中的多元整体性。在这个人类意识与价值体系演进的可视化模型中,“觉醒”思维处于所谓共情式多元主义的层级,既具有包容性与整合性,却又可悲地倾向于与螺旋模型的底层脱节。因此,我通过同时运用这两种观看模式,试图揭示再现秩序中本应隐而不显的内涵。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解读方式,而我的兴趣正在于让它们彼此交锋。
 《五彩纸屑》(工作墙)
《五彩纸屑》(工作墙)
(JP)这种凝视的对峙以何种方式对绘画性记录的本质与正当性提出质询?
(DC)这种对立实质上是图像中被定义与超定义层面之间的博弈。当多元化的后现代阶段试图更清晰地界定某种事物(往往是不公正现象)时,原本被定义的东西由此转化为超定义状态。构图各层级间的关系随之被悉数解读为冲突,这正是采用觉醒视角时必然发生的现象。因此那些与我相遇的母题(我从不主动寻找)往往呈现简单化特质——似乎它们的表达意图过于直白。超定义与高度意识化具有相同的僵化效应,这种原理在抽象语言与生活语言的衔接中同样重现:当抽象语言试图反过来改造思想时,偶尔发生的误用可能导致严厉的反噬。语言本应助人看清,在此却成了盲目的存在。
(JP)悖论的是,你所倚赖的图像叙事体系并不现实主义,反而指向对场景与主体的夸张理想化。面对《五彩纸屑》的图像,我们不禁联想到我们不禁联想到十九世纪留传下来的那些宏伟历史壁画。您如何看待这种对绘画传统的再激活在建构批判性凝视中的作用?
(DC)的确,《五彩纸屑》复兴了19世纪历史绘画的传统——宏伟的效果与漫不经心的异域情调。我们明确成为这幅画作语境中的游客,保持着超然姿态,继而从高处俯视。事实上,这种浮夸风格达到顶峰的世纪,恰好也是殖民扩张、工业革命以及摄影术发明的时代,这绝非偶然。我被历史绘画中所传达的虚假华丽所吸引,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与投影机之弱的某种类比。投射的光线本身并无光辉——这正是影像的悖论:一旦停止投影,一切就终止了。

大卫·克拉耶博 《五彩纸屑》(2015-2018)影像截图 双频影像投影、3D动画(彩色、无声) 18分25秒 图片来源:艺术家和施博尔画廊柏林/巴黎/首尔, ©艺术家
(JP)当所有人物都沉浸在近乎疯狂的类精神性状态时,一个黑人孩子却游离于群体之外开始嘶喊。这个惊恐的角色在场景中究竟承担何种功能?
(DC)这个孩子尖叫的场景,恰恰把我们带回“寂静”。在我看来,寂静最好的表现手法恰恰是这声未被听见的呼喊,它为寂静的空间注入了呼吸。这个孩子仿佛在彩带的重压下自我保护。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得不到任何答案的未竟感官冲动。与此同时,构图中所有绘画性元素——色彩、服饰、场景——却过于轻易地提供着答案。这点一直让我着迷。在《越南,1967,德福附近,重建自峰弘道》(2000)中也能看到类似表达。图像的明晰性能否与某种阻止其意义闭合的元素共存?没有什么比把一幅图像“封死”更糟糕。我甚至把那看作一种“罪”。

 《五彩纸屑》(创作流程截图)
《五彩纸屑》(创作流程截图)
(JP)您所说的“把图像封死”,是什么意思?
(DC)这意味着剥夺图像的多义性与偶然性。当我们强行显现本应隐含的内容时,发生的正是这种剥夺。当然,被剥夺的不是图像本身,而是再度审视的可能。“觉醒”(woke)时代往往使语言的精妙性过度直白化。启蒙时代同样是过度曝光的时代,仅凭话语的力量就导致了最恶劣的暴行。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人们试图为本可保持动态特质的事物赋予固定坐标。耐人寻味的是,当下我们正处于一个所有信息源都依赖IP地址、虚拟图像的每个像素都由坐标确定的时代。3D等新视觉技术的动态特性,正与所有生命形态与生俱来的动态本质形成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
(JP)这部影片如同一个自足的环境,经由显微镜的放大镜头被观看。彩屑这一母题回归悬浮粒子状态,由此揭示图像的复合性。它在构图的视觉秩序中引入视觉噪声,即对信号的扰动。就此而言,这些粒子如何使您得以澄清这些图像赖以生成的技术母体?
(DC)随着视频投影技术的发展,信号变得近乎“绝对静止”。可一旦我们意识到支撑它的那套赫兹频率循环,体内就会生出一种“噪声”,原本的静止变得紧张。回看整体,我们自以为稳定的技术——屏幕、投影机、电灯——其实共享同样的频率;它们包围着我们,规定我们和时间的关系,左右我们的日常行为。噪声与稳定并非对立,而是动态关联;频率让我们感知运动。但悖论在于:若我们过度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反而可能被固定住。这正是我在“时长”问题上常思考的点。“超数字化/超高清”带来的表面安宁容易让人忘了,万物其实由频率与时间流的断点构成。随后或许是一种深睡般的状态,像温和的冥想。这也是合成影像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大卫·克拉耶博 《五彩纸屑》(2015-2018)影像截图 双频影像投影、3D动画(彩色、无声) 18分25秒 图片来源:艺术家和施博尔画廊柏林/巴黎/首尔, ©艺术家
(JP)《五彩纸屑》被构想为“双屏”装置。这种对影像的戏剧化处理,似乎是一种对政治再现方式的再舞台化。采取这种结构,您再次赋予观者在图像阐释中的能动角色。
(DC)每次呈现《五彩纸屑》时,我都会尝试在构成装置的两块屏幕之间制造空隙。我试图让观者难以同时观察构图中全部细节。这样,我便能将影片所依托的碎片化原则付诸实现。这同时也是一种相当寻常、甚至有些平庸的将影像戏剧化的方式。不过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把自己看作以雕塑性方式来对待装置的人。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光的投射现象,我又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雕塑家——前提是把那种自以为是太阳替身的电子光源所具有的僭越性的脆弱纳入考量。从某种意义上,我在雕刻这一拟像。像《影子》(Shadow Piece, 2005)就已经处理过投影机那种自以为雄伟、如日般高贵却又孱弱的特性。最后别忘了:投影中最重要的是观者,不是光源,更不是屏幕表面。把投影技术与观者割裂开来,是一种常见的误解。观者的生理机制决定了一切;我们太常以为技术可以自顾自地运作。在影像装置里,我并不试图攫取观众的注意力——你得先让它走失,才能继续一起上路。